[紀錄片] 解讀「感動」
郭力昕的文章「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」,文章對「生命」的批評其實分為兩個,第一個是首段說的「我認為『生命』是一部存有許多問題與爭議的紀錄作品」,就這一點來說,我不否認如果好好討論的話,可以激盪出許多不同意見,讓探討紀錄片的角度增加。
不過就像郭所說,「生命」需要被好好討論,免得只有過分簡單的感動論述,同樣的,我認為,郭文對紀錄片的看法一樣要好好討論,否則也只是加深了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與偏見。
雖然郭的文章標題下得很有氣勢,郭文的第二個批評:「紀錄片不是贖罪券」,其實沒有像批評「生命」本身那樣,有經過仔細鋪陳,只是簡短地出現在後三段,可能因為匆忙,而沒有好好地推敲。
郭最後問的是為什麼「感動論述」如此盛行?這是個好提問,但我不知道他真正要質疑的是什麼,尤其是他提出的說法,與其說是論證,不如說是還有待證明的假設。
郭把這次「生命」放映引發的「感動論述」和五年前九二一大地震後的「愛心論述」相提並論,由此來引出他的批判,不過一開始的假設就有待證明,由此假設引發的批判更是越偏越遠。
郭文把五年前的「愛心論述」,視為「全國的眾多倖存者,在集體的罪惡感之中紛紛捐款賑災」,這個推論真的是很有問題,我看來看去,都覺得這個論點還有待證明,大家真的是因為罪惡感而捐款嗎?
這個讓我存疑的論點,郭卻拿來當成確切的說法,於是五年後「生命」放映時的感動論述,也只能是呼應五年前倖存者的罪惡感,紀錄片在郭眼中也變成是進教堂膜拜好拿取的贖罪券。
不過,去過「生命」放映現場或是觀察網路上諸多的觀後感,老實說,實在找不出有幾個人在「爭相呼喊『我們能做些什麼』」,也沒有幾個人說要捐款賑災,我狐疑郭到底是從哪裡得出,觀眾是為了洗滌罪惡才去看「生命」?
好像只有李幼新說過他有罪惡感(見此篇),不過李幼新的罪惡感也不是來自於倖存者的心態,而是來自於未能赴災區親身實踐的知識份子負疚感。這個自認有罪惡感的知識份子反而很抗拒去看「生命」,一點都不像郭所預期的,趕著去拿贖罪券來洗滌罪惡。
相反地,大部分觀眾的反應正是郭期許紀錄片應該扮演的角色之一:在「人性與情緒之複雜性上,讓人們獲得深刻一層的認識」,我想「生命」有做到郭說的這一點,所以實在看不出來他在質疑什麼?
郭以為大家去看「生命」是為了減輕罪惡感,因此把觀眾看完後的感動誤認為「消費性的感動」,搞清楚郭這個錯置之後,本文對他的評論也就可以結束了。
郭雖然呼籲大家不要那麼快產生一致、齊一化的觀影反應,看來他自己免不了也犯了這個「齊一化」的毛病。
我認為,有問題的不是「感動」,問題出在於「解讀」,郭想質疑的應該是這一點才對。
比如,有政治人物看完「生命」後,解讀成災民都重生了、政府有做出成績,這個解讀當然是很粗暴,一點都沒有反省政府該負的責任,實在應該大力譴責。
不過,郭其實還是問對了問題,那就是「為什麼『生命』能夠引發這麼大的感動風潮,在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含意是什麼」?
我想,要好好地正視觀眾看完「生命」後引發的感動,掌握這「感動」在觀影者心中的真正樣貌,我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。
如果把人們心中的感動草率誤讀成「消費性的感動」,那才是妨礙了我們在社會文化層面上對這「感動」的探討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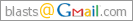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