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紀錄片] 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成了評論的魔障
郭力昕10月12日刊登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文章「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」(註一),可說是自吳乙峰的「生命」上映以來,最不客氣的批評,不過我要指出, 看似犀利的評論,其實立論在對紀錄片過時的刻板印象上,甚至暴露了郭對紀錄片拍攝過程的理解非常浮面,以及對於觀影者多樣化的感動深度的無視與傲慢心態。
首先,郭先指控吳乙峰在題材的選擇上,刻意以討好大眾的底層庶民為對象,對他們的生命情境賦予一種齊一化的理解,似乎淪為剝削他人的廉價紀錄片。
這個嚴厲指控是否公允,恐怕得先弄清楚吳在本片的敘事手法與意圖,才能評斷是否吳賦予這部紀錄片的意義太過單一,還是,這種齊一化的理解,根本上是來自於大眾傳媒與政治人物的輕率解讀、或是某些評論者如郭,錯讀了本片的豐富訊息,才使得對本片的理解齊一化。
郭在文中正確地指出,被攝者本身的感人題材與導演的處理手法是有分別的,但是,就在接下來郭批評導演處理手法的段落中,他對紀錄片的刻板認識成了妨礙他深入評論的障礙。
其 實,「訪談、字幕、與和友人虛擬對話的旁白設計」正是吳為了要「使題材產生的撞擊力更強」而做的處理手法,郭似乎完全不願意理解這種手法對呈顯本片主題 的深刻效果,反而執著於所謂「生活中的影像材料」,認為這些影像材料比訪談、旁白更優越可取,於是輕率地質問起吳是否畫面拍得不夠多。
畫面拍得夠不夠多?這的確是個傲慢輕率的質問。拍攝紀錄片並不是將被攝者置於類似「楚門的世界」的透明情境,或是如狗仔隊般24小時地貼身跟拍。其實就算什麼畫面都有,未必足以自傲,也許拍到的都是如大眾傳媒那種冷冰冰的嗜血畫面。
必須要在這裡特地強調的是,導演與被攝者之間的信任關係,使得被攝者願意對導演揭露的內心世界,比有沒有畫面來得更重要。正是這樣的信任關係建立後,吳的紀錄片才開始發展。
郭 質問導演為什麼沒有拍攝挖到國揚女兒遺體的畫面,其實真正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有沒有這個畫面,而是有沒有必要在片中呈現出這個「挖到遺體」的畫面?郭一 方面宣稱要檢視吳的處理手法,一方面卻在應該展現自己對紀錄片處理手法的獨特見解時,落到執著於「有沒有畫面」的層次,並沒有提升到能夠清楚解析導演手法 的評論高度,批評因此落入空處。
很清楚地,沒有這個挖到遺體的畫面,並無礙於吳處理「生命」的主題,相反地,該片當中並沒有任何一個亡者的遺體畫面,有的只是喪禮上的相片以及生者對死者的記憶、夢境、談論、思念與內心的對話。郭難道看不出來,遺體畫面的有無,對本片來說,是無關宏旨。
或許有人會說,郭在評論前如果先向導演查證過是否有無這個畫面,爭議就可以解決了,但這並不是我質疑他的重點。會把「有無畫面」當成問題提出來,進而把「沒有畫面」當成缺陷來攻擊,徹底暴露了郭對紀錄片的認識,真的很淺。
其 實,對導演的處理手法,我們還有不同的對比可以依據,吳在全景本次放映中,還有另一支片子「天下第一家」,這是一支與「生命」的處理手法截然不同的紀錄 片,「天下第一家」沒有導演的主觀介入、沒有導演喃喃自語的虛擬旁白對話,我們可以試著想想,是否「生命」用這樣客觀、平實的處理手法會更有力量?我想同 時看過這兩部的人,自己會有評斷。
接下來,郭開始批評「生命」片中他所謂的道德爭議,他的批評有三點,但第一點和第二點其實是同一點,就是批評導演的介入與設計。
我必須說,正是這個「導演的介入與設計」,今天「生命」才是我們看到的「生命」,沒有這個介入與設計,「生命」就不成為「生命」了。
對於不能理解或接受「導演的介入與設計」的評論者來說,這正是「生命」最大的爭議所在,但覺得這種處理手法有爭議的人,大半是持著對紀錄片必須客觀的刻板印象,在心中先排斥這樣的介入與設計,不願花心思去理解、深思吳這樣處理的意圖與效果。
想要成為一個稱職的評論者,起碼也要先看懂導演的手法與意圖,然後再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,否則,很容易淪為以一己的偏好或偏見,來評斷他人作品的好壞,這種評論是很粗暴的,對導演並不公平。
吳在本片的介入有好幾個身分,一是身為老病父親的人子、一是拍攝921罹難者家屬的紀錄片工作者,因此,在片子中,導演與其他四個家庭一樣,都成了片子記錄的對象,而紀錄片工作者本身的記錄歷程與感想,也同步地在片中被揭露出來。
吳 的多重身分與921罹難者家屬各自不同的生命經驗,主要是透過虛擬與友人的對話通信來交織平衡,這個形式的設計,巧妙地取代了導演單向的旁白,並且不抵 觸「生命」的主題,反而暗暗地呼應了生者懷念死者的一種慣常反應:將死去的親人當成在虛擬的空間中仍然活著、可以在內心與之對話、溝通。
因 此,吳首先處理的是921罹難者家屬面臨著親人生命的驟逝,這種「斷裂」該如何面對、填補,先是等待著尋找遺體,這其中有記憶、有夢境,再藉著導演與父 親的關係,拉開來思索這種「不在者仍在、在者卻已不在」的複雜性,隨著時間流逝,鏡頭追隨著各個家庭的發展軌跡,其中有思念、有談論、有逃避、有憤怒,當 然,也各自找著了處理方式與出口。
四個家庭各自的出口,正如火車行進中隧道明暗相間的影像所暗示的,是出口,也是生命中暫時的過程。吳並沒有意圖要給出一個關於生命意義的特定答案,只是呈現出被攝者的經歷與他的思索過程,生命的意義毋寧是留待觀影者自行去咀嚼的。
片子將近結束時,導演透過邀請被攝者寫信的方式,來宣洩她們對親人的懷念,這個設計,接替了他與友人對話的嘎然終止,成為一種結構上的總結。最後更揭露出與他通信的友人身分,意圖讓觀影者在片末重新回頭思索本片的主旨何在,而死者其實永遠活在我們生者心中的某個角落。
這個邀請被攝者寫信的動作,跟友人的身分一樣,也在片中由導演自行揭露,吳並不隱藏紀錄片工作者這個角色,反而透過揭露記錄的過程,增添了本片額外的層面與深度。
郭認為吳的介入,顯得矯情與自我中心,甚至有些評論者認為,吳意圖主導觀眾對生命的看法,這都是不夠了解這個介入所產生的觀影效果,才會出現的誤解。
誠 如某些評論者所說,「生命」抽離了地震當下的社會脈絡,而且吳的介入與設計使得「生命」不再是921的紀錄片,但這並不會使得921僅僅成為吳乙峰心情 獨白的背景(註二),這四個家庭各自呈顯的影像力量都相當強烈,反而吳與老父的經歷、或是吳與友人的通信,其實強度並不足以掩蓋罹難者家屬的經歷,甚至有 些偏弱,不足以抵抗平衡罹難者家屬的力量,因此有的評論者對吳的介入與設計產生懷疑,認為沒有必要。
那麼,為何吳還是要跳出來?我認為, 正是吳放入了自身的經驗,以及呈現出作為記錄者的反省,一步步地卸下觀影者觀看他人故事的預設心態,帶領觀影者像他一 樣,回頭反思自己的生命經驗,透過吳的介入與設計,觀影者不再是一個觀看921地震災難奇觀的他人,反而透過對自身生命經驗的反省,與921罹難者家屬的 經驗產生同理心的理解。唯有這樣的同理心出現,我們才能說,觀影的國人真正地理解了921大地震所帶來的心理創傷。
這樣的反省與同理心,正是「生命」在放映後那種強大的感動能量的來源,觀影者隨著導演的介入,會在片中的某個不特定點與自身的生命連結,從而或深或淺地被打動。
並不是導演刻意去操作這種感動,這麼多觀影者本身湧出的感動,在公開放映前,其實也在導演意料之外,否則他不會焦慮有沒有觀眾要來看,而這個感動所引發的口耳相傳,才是「生命」的放映熱度能夠延燒不斷的主因,政治人物的捧場與媒體報導只具有錦上添花的效果。
這 種感動既是透過觀影者的反省與同理心,它連結著每個人不同的生命體驗與經歷,有時候這感動可以清楚說出,有時候又太過私密而無從說明,這些感動其實具有 多樣化的面貌與深度,無法被輕率地解釋為僅是一種消費性的感動(註三),認為這種感動一定是膚淺的,毋寧是一種菁英心態的傲慢。
正是吳在「生命」的介入與設計,使得我們不再僅是「旁觀他人之痛苦」,我們也同時看到了自己的痛苦,進而彼此理解,而不同層面的觀影群眾,更使得這樣的觀影反應不至於齊一化。
其實只是媒體、政治人物與文化菁英在消費「生命」所帶來的感動,對於到戲院去觀賞的不同年齡、不同階層的觀影者來說,這樣的批判實在太過廉價。
因 此,並不是對「生命」的感動有問題,而是「生命」被單單地抽離出「全景映像季」的整體脈絡,使得這感動掩蓋了全景對921的真實記錄,全景其實是這「感 動熱潮」的受害者,而不是操作這個郭所謂的「感動論述」的始作俑者。媒體、政治人物與文化菁英粗暴地消費「生命」,抽離整體脈絡,再來歸咎吳不該拍這個讓 人感動到不行的片子,倒果為因也太甚了。
郭一方面粗糙地將觀影者的感動貶為消費性,一方面又不忘故做姿態地出來指導大眾,看紀錄片不是要為了「獲取贖罪券」,感動產生不了「有政治意義的行動」,反而更可能「帶來對結構性問題更大的漠然與冷酷」。
老 實說,這種「眾人皆睡我獨醒」的評論太輕易,真正要問的是,如何把觀影者已被激起的感動,轉化到具體的行動上,不論是網路上諸多寫手呼籲大家去看「全景 映像季」的其他片子,或是全景本身明年要舉辦研討會的計畫,都是嘗試將感動導向行動的小小努力。知識份子若是不能親身參與實踐、或是提出更具創意、具體的 行動計畫,只是高傲地指責眾人,這種菁英姿態太容易擺了,一樣無助於解決問題,更有愧於知識份子的責任。
最後,郭對吳的第三點道德質疑,是將紀錄片工作者與被拍攝者的關係看得太過片面,這種質疑根本無視於紀錄片田野現場的複雜性,其實也就是人與人彼此之間關係的複雜性。
紀錄片工作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,必須看作是隨著時間發展的整體過程,其中有拒絕與誤解,也有說服與溝通、陪伴與信賴等等複雜層面,要切開來任意挑出一點來批判,根本是不可能的(註四)。這就好像外人單單只看夫妻間的一場爭吵,就判定夫妻關係有問題,這是很可笑的。
至於斤斤計較於被記錄者是否願意被拍攝,或是認為紀錄片工作者說服被拍攝者接受記錄是種利用、剝削,這種將事情簡單化的說法,無視於被拍攝者本身隱含著想表達的意圖(註五),紀錄片其實也可能是導演與被拍攝者的共謀演出。
紀錄片工作者與被拍攝者的關係,一直都是紀錄片裡頭被永恆探討的問題,它無法一勞永逸的解決其中的矛盾,給出一個特定的解決方案。要探索這個問題,只能個案式地檢視每部紀錄片的整體拍攝過程,想要抽象地依據某種道德規則來批判,都是粗暴可鄙的。
而紀錄片工作者所面臨的問題,其實也同樣是新聞、報導文學所面臨的問題,凡是要去記錄他人真實經歷的作者,都免不了這些永恆的質問,但在粗暴地質問作者之前,搞清楚這個議題的複雜性,應該是一個評論者必備的修養與責任。
註:
1. 郭力昕文章的原始連結為此,如果中國時報移除了這個連結,可參考苦勞網上的轉載, 但兩者版本不同,苦勞網上的內文比報紙刊出的較長,應是郭的原始完整版本。
2. 參考 munch 的「生命 ─ 災區獨白與城市救贖」。 他對吳乙峰與觀眾心態的批評,某種程度來說,與郭的誤解是一樣的。
3. 參考柳澄之的「《生命》--用影像敘事帶動世代的認同與療癒」 。更多觀影者的感想,可參考紀錄片公園的蒐集。
4. 參考朱賢哲的「流浪狗紀錄片日記」。並不是所有的記錄者都能完整的揭露與被拍攝者的關係,有些相處過程會涉及隱私,並不適合對大眾揭露。
5. 參考黃文雄的「不要錯過《生命》」,對他父親接受訪問的描述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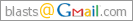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